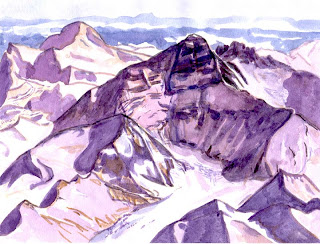2009年1月29日
南湖大山縱走中央尖 1969
南湖大山縱走中央尖山
日期: 1969/7/6~13
隊員 : 黃一元(隊長)、葉陶然、紀清輝、阮光澤、柯志睿、廖芳男、葉庶交、馬鴻榮、張文溪、王進福、王詩吟、袁國新、許斯然及吳朝木。
嚮導: 陳文章 黑杜(四季山胞)
費用:450元(糧食,山胞,來回車資)
行程:
7月6日 (日)晴
台北火車站---宜蘭---四季(接兩位山胞)---南山(宿南山衛生所)1156M
7月7日 (一)晴
南山---耶克糾溪---美莫康溪會合口---登山口---第一茅草屋---上稜---奇烈亭(2570M)
7月8日 (二)晴
奇烈亭---鞍部(3150M)---審馬陣山---南湖北山(3535M)---北峰(3580M)---「南湖山莊」 (3320M)
7月9日 (三)晴
南湖山莊---南湖大山主峰---南下山谷---3440峰支稜松林---中央尖山最後獵寮
7月10日 (四)晴
中央尖溪休息日
7月11日 (五)晴
中央尖山最後獵寮---3500M鞍部---中央尖山---中央尖山最後獵寮
7月12日 (六)晴
中央尖山最後獵寮---南湖溪---中央尖溪南湖溪會流處---大峽谷---2734峰下溪床
7月13日 (日)晴
溪床上鞍部---2734峰鞍部---林道---思源啞口---南山---宜蘭---台北

日期: 1969/7/6~13
隊員 : 黃一元(隊長)、葉陶然、紀清輝、阮光澤、柯志睿、廖芳男、葉庶交、馬鴻榮、張文溪、王進福、王詩吟、袁國新、許斯然及吳朝木。
嚮導: 陳文章 黑杜(四季山胞)
費用:450元(糧食,山胞,來回車資)
行程:
7月6日 (日)晴
台北火車站---宜蘭---四季(接兩位山胞)---南山(宿南山衛生所)1156M
7月7日 (一)晴
南山---耶克糾溪---美莫康溪會合口---登山口---第一茅草屋---上稜---奇烈亭(2570M)
7月8日 (二)晴
奇烈亭---鞍部(3150M)---審馬陣山---南湖北山(3535M)---北峰(3580M)---「南湖山莊」 (3320M)
7月9日 (三)晴
南湖山莊---南湖大山主峰---南下山谷---3440峰支稜松林---中央尖山最後獵寮
7月10日 (四)晴
中央尖溪休息日
7月11日 (五)晴
中央尖山最後獵寮---3500M鞍部---中央尖山---中央尖山最後獵寮
7月12日 (六)晴
中央尖山最後獵寮---南湖溪---中央尖溪南湖溪會流處---大峽谷---2734峰下溪床
7月13日 (日)晴
溪床上鞍部---2734峰鞍部---林道---思源啞口---南山---宜蘭---台北

2009年1月28日
“Chiao Sheng”
 圖/(由左至右)蔡光隆(蔡爸爸),蔡文宗,蔡國彥(小傢伙),陶維極(作者),張文溪(譯者)
圖/(由左至右)蔡光隆(蔡爸爸),蔡文宗,蔡國彥(小傢伙),陶維極(作者),張文溪(譯者)文/陶維極(G.B.Talovich) 1979 Climbing
前言/譯者
陶維極,一位到台灣求學,創業,最後立足於這塊土地的美國人。
山友蔡文中的知友,我就僅知道這麼多,
距發現,開發龍動岩場兩年後,大約是1978年的秋末,雪岩俱樂部的爬岩活動,
這位身材瘦高的美國人跟著蔡醫師一起來。之後,隔了很長一段時間,蔡醫師遞了一份影本給我,這是陶在Climbing雜誌上的發表。
當年就有意翻譯刊載,陶觀察細微,對這次爬岩過程的記憶深刻,早年在龍洞與鼻頭角這塊海灣的人文尤多著墨,這些舊史如今多已隨著公路的貫通而荒沒。
山友蔡文中的知友,我就僅知道這麼多,
距發現,開發龍動岩場兩年後,大約是1978年的秋末,雪岩俱樂部的爬岩活動,
這位身材瘦高的美國人跟著蔡醫師一起來。之後,隔了很長一段時間,蔡醫師遞了一份影本給我,這是陶在Climbing雜誌上的發表。
當年就有意翻譯刊載,陶觀察細微,對這次爬岩過程的記憶深刻,早年在龍洞與鼻頭角這塊海灣的人文尤多著墨,這些舊史如今多已隨著公路的貫通而荒沒。
“Chiao Sheng”是陶在雜誌上用的標題,百思不得其解,既然如此,本譯文援用原文作標題。
原文
蔡,蔡,蔡,張和我,一行五人相約爬岩。
第一位蔡--蔡文宗,牙醫生,來電話邀我與他的朋友到龍洞爬岩。
張文溪(台灣喜馬拉雅遠征隊)與蔡爸爸(蔡光隆)兩人是台灣少數的老手,已有十來年的爬岩。蔡國彥,蔡爸爸的公子,有一個好名子,意思是一國的博學之士,我則直稱他小傢伙,看起來瘦巴巴的六歲小孩,但是爬得比我好很多。
我們搭著蔡爸速霸陸箱型車,先驅北,再從基隆轉東接上東北海岸公路。
車行經過金瓜石下方,山巒起伏,青山柔和,一路看不到有可供爬岩的懸岩峭壁。
金瓜石景緻迷人,日本接收者在占領期間蓋了不少房子建築,在二次大戰末期美軍幾乎為之炸平。公路上方,巨大,黑色三角錐狀「雷霆岩」面向金瓜石。
蔡爸說 :“去年夏天,有兩人來爬這座山。”“在下降時固定點鬆脫了!”
“後來怎麼了?”
蔡爸摳了一下食指,台灣人往生的表示。
車子繞著台灣最東北端腹地狹小的鼻頭角漁港而去,然後引擎再度軌軌叫著穿過燈塔下方的隧道;出了洞口,前面就是陽光燦爛下的龍洞灣。
越過海灣,直線距離一公里外縱列著一排的岩岬。我們計畫攀登第一道岩牆,距離龍洞村不遠,這些岩牆是由海水穿孔的礁岩所形成,龍洞之名便是來自龍游大海的比喻。
我們分成兩支繩隊,蔡爸、小傢伙和我一組,爬這道主壁東面,張和文宗選擇一條新路線。我仔細的觀察蔡爸向上攀爬的一舉一動,因為沒有詳細攀登指導,我必須按照我腦子的警覺來分清狀況。蔡爸已越過上方的凸岩不見蹤影,我則爬的筋疲力絕,眼看著這小傢伙一步步爬上來,身上竟沒上繩子。他頭上帶著一頂橘色編製寬緣帽,風一吹就把帽緣打到眼上。
這孩子身軀十分柔軟,手腳輕捷穩定。
蔡爸在上頭呼叫我上來,小傢伙坐著望著我爬這道5.9的路線,小鬼!在你面前出糗門都沒有!我一口氣越過上方的凸岩,將自己位置固定好:小鬼,上來吧!
爬到岩壁的北面時,看到張的繩子橫在我的前頭,張和蔡爸兩人在視線之外
“喂!怎麼一回事?”
文宗正在我下方,歪著頭側身研判,熱誠的回應
“那是張的路線”
蔡爸從邊緣探出臉來“從繩子下面穿過去,然後找個地方停下來等文宗過去。”“喂!張!把繩子放鬆一些好不好!”
我從白色的繩子移過去,抬頭注視著橫在前面的岩壁。很幸運,我看到一小塊的岩棧,大小可以容得下半個足面,上頭有不錯的把手點,我塞進一具岩楔固定自己,蔡爸再解除確保,我掛在上頭乾等文宗爬過去。
回想我在求學那個時代,此地只能有船隻靠岸,另外就是一條彎彎曲曲的海邊步道,我曾經夏天在海岬另一頭露營,可靠的Stephenson帳篷與我度過星夜,不但要躲蚊子,海防衛兵,還要與走私客周旋。
但是,那些日子卻是多采多姿,令人心亂情迷,放眼全是奇異怪誕的幻想世界,成天陶醉在清澄藍色的大海,礁岩,還有成千上萬色彩炫耀,艷麗非常的熱帶魚。
我一直有爬這到岩壁的念頭,但是始終沒能夠找到夥伴…
文宗在我下方約三公尺,跟著張的這一條路線不太容易,
“文宗!不錯喔!.....嘿!不要碰我的繩子,我會把你打下去!”
我舉起腰上的繩子作勢威嚇
“去你的!”文宗笑著(“收起來!”)別過頭去,
“我來找一些樹枝給你在上面作個巢”
“爬你的吧,王八蛋”
“搞甚麼,你不喜歡嗎?你活得不耐煩?好啊,你可以走了。”
他終於上去了,故意抓著繩子猛的拉著一把,我死命的抓著固定繩。
文宗提議:“就稱是張的新路線Chiao Sheng—Crossed Rope。”
我倒另有想法,我不想說出來,看著他的腳踝,跟著一腳越過我的頭。
我打進一根岩楔作固定點,然後呼叫小傢伙爬上來。
看他輕鬆就爬上來,心想我好像有爬了不止兩倍高,真想趁人不注意時一腳把他踹下去
。
一夥人齊聚在頂上午餐,放眼過去,鼻頭角燈塔就坐落在海灣之上的海岬。我可以一眼認出海灣另一邊的古道,現已難以肉眼辨認。舊道經燈塔有捷徑直接下到竹林,然後從人家的豬舍出來。
那個時代,外地人很少見,健行者也不普遍。
一位大鼻子阿兜仔(作者自稱)的背包旅行者小心翼翼,躡手躡腳的穿經豬欄,一名居民正好提著一桶餿水來餵豬,一頭撞見這位全身邋遢不整,如迷樣的西洋人,
這位住民當場差點給嚇死。
飯後,我們挑了後面一條草坡上去,希望容易離開這個地方,不料遇到海防的崗哨,舉著上了刺刀的步槍,示意要我們退回。
“XXX”有人不滿的抱怨
“你們要有同理心,我敢打賭這位阿兵哥必定頭一遭碰到。”
“是啊,我打賭他今天有事做了,他可有東西可以往上作報告。”
大家都不願意垂降,我們選了容易不用繩索的北面倒爬下去。蔡爸帶頭下去,我殿後。經過一條稍微外懸的橫渡,大家都輕易的過去了,我180公分的身材卻遇到難題,當我發現時已經晚了,我的肩髈已卡在外傾的岩壁上。
我曲驅彎著腰背,試著在岩棧上移動雙腳,我發狂似地把整條手臂塞進裂縫中,兩腳試著在岩棧上找穩當的依靠,為了貼住一小凸塊,兩腳成O向內彎,在左側找到一個把手點,甚至用我的鼻子來支撐,最後我沒輒了,
“我卡住了”對著裂縫,緊張的幾乎不能呼吸。
“不要動”蔡爸大叫“我上來替你確保”
他輕捷的越過我,正確的說,就在我的上頭爬過去,因為我就是緊緊的貼在一條垂直的裂隙上部。蔡爸小心的從我背上越過,在我的腰部附近及肩上方找把手點,小心翼翼的避免踏在我的頭上。張上到我下方,引導我退向左側,以便能夠援繩上去。移到上方安全的岩層後,僵硬的左臂才得到紓解,接著我用肋骨抵住。
再次試著橫移,卻始終無法硬擠過去,最後,我墜落了,蔡爸迅速一把抓住。
最後沿著蔡爸上來的裂隙倒爬下去,這下我的隨隊醫生有事做了。文宗檢查我的傷勢,然後對著我說,有兩顆牙要補,可能會拔掉一顆。
發生這件事件後,小傢伙也需要繩索保護攀登。文宗誤判距離,跳下最後幾公尺時扭傷了腳踝。這下我的心情感覺好多了。
這下午,小傢伙沒事專找哪些無辜的鳥兒殺時間,手上抓著大大的石頭就丟。冥冥中似乎會給你呼應,無巧不巧,丟擲出去的一顆石頭,從岩壁反彈回來,正好打在他頭上。文宗和我,一個跛腳,一個受傷,兩人趴在大石頭上看著張與蔡爸兩人在岩塔上上下下。
耳邊不時交互響起海浪擊石的脆裂聲,登山鞋在岩石上ㄔㄔ磨擦聲,昏昏沉沉中,好像有一尾活潑發亮的魚兒戴著橘色的帽子在岩石上繃繃跳跳。
第一位蔡--蔡文宗,牙醫生,來電話邀我與他的朋友到龍洞爬岩。
張文溪(台灣喜馬拉雅遠征隊)與蔡爸爸(蔡光隆)兩人是台灣少數的老手,已有十來年的爬岩。蔡國彥,蔡爸爸的公子,有一個好名子,意思是一國的博學之士,我則直稱他小傢伙,看起來瘦巴巴的六歲小孩,但是爬得比我好很多。
我們搭著蔡爸速霸陸箱型車,先驅北,再從基隆轉東接上東北海岸公路。
車行經過金瓜石下方,山巒起伏,青山柔和,一路看不到有可供爬岩的懸岩峭壁。
金瓜石景緻迷人,日本接收者在占領期間蓋了不少房子建築,在二次大戰末期美軍幾乎為之炸平。公路上方,巨大,黑色三角錐狀「雷霆岩」面向金瓜石。
蔡爸說 :“去年夏天,有兩人來爬這座山。”“在下降時固定點鬆脫了!”
“後來怎麼了?”
蔡爸摳了一下食指,台灣人往生的表示。
車子繞著台灣最東北端腹地狹小的鼻頭角漁港而去,然後引擎再度軌軌叫著穿過燈塔下方的隧道;出了洞口,前面就是陽光燦爛下的龍洞灣。
越過海灣,直線距離一公里外縱列著一排的岩岬。我們計畫攀登第一道岩牆,距離龍洞村不遠,這些岩牆是由海水穿孔的礁岩所形成,龍洞之名便是來自龍游大海的比喻。
我們分成兩支繩隊,蔡爸、小傢伙和我一組,爬這道主壁東面,張和文宗選擇一條新路線。我仔細的觀察蔡爸向上攀爬的一舉一動,因為沒有詳細攀登指導,我必須按照我腦子的警覺來分清狀況。蔡爸已越過上方的凸岩不見蹤影,我則爬的筋疲力絕,眼看著這小傢伙一步步爬上來,身上竟沒上繩子。他頭上帶著一頂橘色編製寬緣帽,風一吹就把帽緣打到眼上。
這孩子身軀十分柔軟,手腳輕捷穩定。
蔡爸在上頭呼叫我上來,小傢伙坐著望著我爬這道5.9的路線,小鬼!在你面前出糗門都沒有!我一口氣越過上方的凸岩,將自己位置固定好:小鬼,上來吧!
爬到岩壁的北面時,看到張的繩子橫在我的前頭,張和蔡爸兩人在視線之外
“喂!怎麼一回事?”
文宗正在我下方,歪著頭側身研判,熱誠的回應
“那是張的路線”
蔡爸從邊緣探出臉來“從繩子下面穿過去,然後找個地方停下來等文宗過去。”“喂!張!把繩子放鬆一些好不好!”
我從白色的繩子移過去,抬頭注視著橫在前面的岩壁。很幸運,我看到一小塊的岩棧,大小可以容得下半個足面,上頭有不錯的把手點,我塞進一具岩楔固定自己,蔡爸再解除確保,我掛在上頭乾等文宗爬過去。
回想我在求學那個時代,此地只能有船隻靠岸,另外就是一條彎彎曲曲的海邊步道,我曾經夏天在海岬另一頭露營,可靠的Stephenson帳篷與我度過星夜,不但要躲蚊子,海防衛兵,還要與走私客周旋。
但是,那些日子卻是多采多姿,令人心亂情迷,放眼全是奇異怪誕的幻想世界,成天陶醉在清澄藍色的大海,礁岩,還有成千上萬色彩炫耀,艷麗非常的熱帶魚。
我一直有爬這到岩壁的念頭,但是始終沒能夠找到夥伴…
文宗在我下方約三公尺,跟著張的這一條路線不太容易,
“文宗!不錯喔!.....嘿!不要碰我的繩子,我會把你打下去!”
我舉起腰上的繩子作勢威嚇
“去你的!”文宗笑著(“收起來!”)別過頭去,
“我來找一些樹枝給你在上面作個巢”
“爬你的吧,王八蛋”
“搞甚麼,你不喜歡嗎?你活得不耐煩?好啊,你可以走了。”
他終於上去了,故意抓著繩子猛的拉著一把,我死命的抓著固定繩。
文宗提議:“就稱是張的新路線Chiao Sheng—Crossed Rope。”
我倒另有想法,我不想說出來,看著他的腳踝,跟著一腳越過我的頭。
我打進一根岩楔作固定點,然後呼叫小傢伙爬上來。
看他輕鬆就爬上來,心想我好像有爬了不止兩倍高,真想趁人不注意時一腳把他踹下去
。
一夥人齊聚在頂上午餐,放眼過去,鼻頭角燈塔就坐落在海灣之上的海岬。我可以一眼認出海灣另一邊的古道,現已難以肉眼辨認。舊道經燈塔有捷徑直接下到竹林,然後從人家的豬舍出來。
那個時代,外地人很少見,健行者也不普遍。
一位大鼻子阿兜仔(作者自稱)的背包旅行者小心翼翼,躡手躡腳的穿經豬欄,一名居民正好提著一桶餿水來餵豬,一頭撞見這位全身邋遢不整,如迷樣的西洋人,
這位住民當場差點給嚇死。
飯後,我們挑了後面一條草坡上去,希望容易離開這個地方,不料遇到海防的崗哨,舉著上了刺刀的步槍,示意要我們退回。
“XXX”有人不滿的抱怨
“你們要有同理心,我敢打賭這位阿兵哥必定頭一遭碰到。”
“是啊,我打賭他今天有事做了,他可有東西可以往上作報告。”
大家都不願意垂降,我們選了容易不用繩索的北面倒爬下去。蔡爸帶頭下去,我殿後。經過一條稍微外懸的橫渡,大家都輕易的過去了,我180公分的身材卻遇到難題,當我發現時已經晚了,我的肩髈已卡在外傾的岩壁上。
我曲驅彎著腰背,試著在岩棧上移動雙腳,我發狂似地把整條手臂塞進裂縫中,兩腳試著在岩棧上找穩當的依靠,為了貼住一小凸塊,兩腳成O向內彎,在左側找到一個把手點,甚至用我的鼻子來支撐,最後我沒輒了,
“我卡住了”對著裂縫,緊張的幾乎不能呼吸。
“不要動”蔡爸大叫“我上來替你確保”
他輕捷的越過我,正確的說,就在我的上頭爬過去,因為我就是緊緊的貼在一條垂直的裂隙上部。蔡爸小心的從我背上越過,在我的腰部附近及肩上方找把手點,小心翼翼的避免踏在我的頭上。張上到我下方,引導我退向左側,以便能夠援繩上去。移到上方安全的岩層後,僵硬的左臂才得到紓解,接著我用肋骨抵住。
再次試著橫移,卻始終無法硬擠過去,最後,我墜落了,蔡爸迅速一把抓住。
最後沿著蔡爸上來的裂隙倒爬下去,這下我的隨隊醫生有事做了。文宗檢查我的傷勢,然後對著我說,有兩顆牙要補,可能會拔掉一顆。
發生這件事件後,小傢伙也需要繩索保護攀登。文宗誤判距離,跳下最後幾公尺時扭傷了腳踝。這下我的心情感覺好多了。
這下午,小傢伙沒事專找哪些無辜的鳥兒殺時間,手上抓著大大的石頭就丟。冥冥中似乎會給你呼應,無巧不巧,丟擲出去的一顆石頭,從岩壁反彈回來,正好打在他頭上。文宗和我,一個跛腳,一個受傷,兩人趴在大石頭上看著張與蔡爸兩人在岩塔上上下下。
耳邊不時交互響起海浪擊石的脆裂聲,登山鞋在岩石上ㄔㄔ磨擦聲,昏昏沉沉中,好像有一尾活潑發亮的魚兒戴著橘色的帽子在岩石上繃繃跳跳。
「奇蹟似的玉山救難」

這本小冊記錄「雪岩俱樂部」的伙伴在民國68年 (西元1979)冬天玉山救難的過程。
以小白花(細葉薄雪草Edelweiss)為部徽的「雪岩俱樂部」, 召募同好, 組織了一支含教練共28名的冬訓隊, 選擇臺灣最高峰玉山作為訓練基地。
為進軍喜瑪拉雅山,冬訓隊選擇罕有登山者到臨的玉山北坡駐留, 準備以此作為訓練基地。冬訓隊的第一目標選擇第一雪溝(命名為「劍溝」)登玉山主峰與東峰, 企圖完成國人首次冬期冰雪地自「劍溝」登玉山; 第二個任務: 從北峰翻越主峰風口,在三叉峰設中繼營, 縱走玉山南峰, 作極地登山訓練。
但是1月29日夜晚的墜崖山難發生後, 所訂計劃停頓,冬訓隊的人力資源全部投入救難。
冬訓隊在進駐玉山第五天,即民國六十八年(1979)一月二十九日的下午,三重山協玉山登峰隊四男一女, 隊長林士崇, 為了架好營帳, 在強風中自山頂失足墜落300公尺到達劍溝底部雪坡上,其隊員見狀下去搶救, 結果反而事態擴大, 除林士崇墜落身亡外, 一人失足頭部撞擊重傷, 一人身困雪岩披覆的北壁上下不得, 事發後玉山山區已降下黑夜,情況非常險惡。
冬訓隊義不容辭擔起救難任務, 這個決定阻止了骨牌效應的擴大。
隨後, 最關鍵的三天中,展開了有史以來最迅速的救援行動,民生報記者黃建興在事發當年,還以「一次奇蹟似的玉山救難」為題連載三天導。
冬訓隊貼近現場, 裝備及技術皆足堪勝任, 一時之間立即由冬訓隊伍的型態轉為冰雪地上失事的救難隊伍, 隨後九天, 每天與生命賽跑; 經由全體教練與隊員的通力合作, 救下了困在玉山頂上的四名登山者, 並在北坡上協助挖掘出身故者遺體,最後成功從3600公尺的玉山北壁救下這群無助的愛山者, 完成了我國冬期冰雪地高山艱難的救援任務。
總結129玉山山難能「奇蹟」似圓滿善後,筆者認為有幾個條件決定了本次救援的成敗:
1. 是不幸也是幸運, 冬訓隊的活動地區臨近失事地點,人力裝備充足, 能在遇難後第一時間展開救援, 成功救下困在北壁上的失事者, 防止事態進一步擴大。
2. 冬訓隊帶上了齊全的各式冰雪地形登山器材,如:冰樁、阻雪板、JUMAR、及登山繩等器材;這些器材在運送重傷患郭榮芳下北坡發揮了重大作用。
3. 人力與資源充份支援且及時, 隨隊醫師蔡文宗準備齊全的醫療器材、藥品,從八通關及時趕到, 提供現場急救, 挽救了一條寶貴的生命。
此外, 這場救難人員中若要選出最關鍵人物, 先遣隊長應詩澄(大貓)應居首功。
大貓指揮若定, 人力配置果決,掌握了第一時間救難的黃金要素。多位隊員黃福來﹑蕭宗熙﹑謝世枋﹑林明源﹑張銘隆及洪端祐奮不顧自身安危的勇氣,承擔未曾有過的艱險, 近乎完美的完成每一次的任務,趙志華 徐慶榮﹑黃曙東等人協助挖掘直到救難結束才下山。
玉山救難成功來自「雪岩俱樂部」多年來的自訓與準備, 為的是累積冰雪地登山的能力,並把目標放在喜馬拉雅,但是絕未想到在冬訓剛啟就用盡所有的絕活。
次年(1980年)一元兄再次帶領冬訓隊, 張銘隆謝世枋等人從劍溝登玉山,此舉將台灣的冰雪地登山明朗的宣示開來
這兩次的玉山冬訓奠定了雪岩俱樂部的海外登山活動的信心,1980年一元兄突破瓶頸, 成功帶出我國第一支喜馬拉雅登山隊(Pharachamo 6383m),隨後有筆者1981年春Chulu West ,1981年冬蔡楓彬印度Trisul , 1982年林芳娟尼泊爾Tent Peak女子隊, 1982吳夏雄印度白針峰, 1983李淳容印度Brigupath 新路線張銘隆登頂等喜馬拉雅6000及7000公尺級登山活動。這段期間以至往後十年,台灣山岳界把目標往上放向8000公尺巨峰, 1993年5月傑出的李淳容女士組織兩岸珠穆朗瑪峰登峰隊,吳錦雄成為第一個台灣人登上世界最高峰 - 聖母峰。
散居各地,漂泊無定所, 並無特定組織型式, 以活動為旨趣凝結,回顧「雪岩俱樂部」60年代末開始萌芽, 到80年代中期, 前後達25年的台灣海外登山的黃金時代, 這些當年的「救難英雄」幾乎無役不參。是年在玉山救難的這些隊員, 不但活躍在喜馬拉雅,也多有北美阿拉斯加及南美安地斯的探險登山活動。
不過, 上天並不獨厚這群仁者,大貓在1982年一次車禍中嚴重腿傷,隔年倆位傑出隊友徐慶榮及黃世傑同時在印度喜瑪拉雅的登峰途中失蹤,至今杳無音訊。
去年到苗栗馬拉邦山弔念徐慶榮, 今年(2005)初大貓自美返國,再度勾起了昔日山中共患難的記憶。
始作俑者之一的我, 心想不能忘懷台灣登山史上這一段… 。
讓榮譽歸於勇者, 讓事蹟永留世人; 山岳無情, 前事已難避免,有期後者知所警備,是筆者所願。
張文溪
2005年6月5日
以小白花(細葉薄雪草Edelweiss)為部徽的「雪岩俱樂部」, 召募同好, 組織了一支含教練共28名的冬訓隊, 選擇臺灣最高峰玉山作為訓練基地。
為進軍喜瑪拉雅山,冬訓隊選擇罕有登山者到臨的玉山北坡駐留, 準備以此作為訓練基地。冬訓隊的第一目標選擇第一雪溝(命名為「劍溝」)登玉山主峰與東峰, 企圖完成國人首次冬期冰雪地自「劍溝」登玉山; 第二個任務: 從北峰翻越主峰風口,在三叉峰設中繼營, 縱走玉山南峰, 作極地登山訓練。
但是1月29日夜晚的墜崖山難發生後, 所訂計劃停頓,冬訓隊的人力資源全部投入救難。
冬訓隊在進駐玉山第五天,即民國六十八年(1979)一月二十九日的下午,三重山協玉山登峰隊四男一女, 隊長林士崇, 為了架好營帳, 在強風中自山頂失足墜落300公尺到達劍溝底部雪坡上,其隊員見狀下去搶救, 結果反而事態擴大, 除林士崇墜落身亡外, 一人失足頭部撞擊重傷, 一人身困雪岩披覆的北壁上下不得, 事發後玉山山區已降下黑夜,情況非常險惡。
冬訓隊義不容辭擔起救難任務, 這個決定阻止了骨牌效應的擴大。
隨後, 最關鍵的三天中,展開了有史以來最迅速的救援行動,民生報記者黃建興在事發當年,還以「一次奇蹟似的玉山救難」為題連載三天導。
冬訓隊貼近現場, 裝備及技術皆足堪勝任, 一時之間立即由冬訓隊伍的型態轉為冰雪地上失事的救難隊伍, 隨後九天, 每天與生命賽跑; 經由全體教練與隊員的通力合作, 救下了困在玉山頂上的四名登山者, 並在北坡上協助挖掘出身故者遺體,最後成功從3600公尺的玉山北壁救下這群無助的愛山者, 完成了我國冬期冰雪地高山艱難的救援任務。
總結129玉山山難能「奇蹟」似圓滿善後,筆者認為有幾個條件決定了本次救援的成敗:
1. 是不幸也是幸運, 冬訓隊的活動地區臨近失事地點,人力裝備充足, 能在遇難後第一時間展開救援, 成功救下困在北壁上的失事者, 防止事態進一步擴大。
2. 冬訓隊帶上了齊全的各式冰雪地形登山器材,如:冰樁、阻雪板、JUMAR、及登山繩等器材;這些器材在運送重傷患郭榮芳下北坡發揮了重大作用。
3. 人力與資源充份支援且及時, 隨隊醫師蔡文宗準備齊全的醫療器材、藥品,從八通關及時趕到, 提供現場急救, 挽救了一條寶貴的生命。
此外, 這場救難人員中若要選出最關鍵人物, 先遣隊長應詩澄(大貓)應居首功。
大貓指揮若定, 人力配置果決,掌握了第一時間救難的黃金要素。多位隊員黃福來﹑蕭宗熙﹑謝世枋﹑林明源﹑張銘隆及洪端祐奮不顧自身安危的勇氣,承擔未曾有過的艱險, 近乎完美的完成每一次的任務,趙志華 徐慶榮﹑黃曙東等人協助挖掘直到救難結束才下山。
玉山救難成功來自「雪岩俱樂部」多年來的自訓與準備, 為的是累積冰雪地登山的能力,並把目標放在喜馬拉雅,但是絕未想到在冬訓剛啟就用盡所有的絕活。
次年(1980年)一元兄再次帶領冬訓隊, 張銘隆謝世枋等人從劍溝登玉山,此舉將台灣的冰雪地登山明朗的宣示開來
這兩次的玉山冬訓奠定了雪岩俱樂部的海外登山活動的信心,1980年一元兄突破瓶頸, 成功帶出我國第一支喜馬拉雅登山隊(Pharachamo 6383m),隨後有筆者1981年春Chulu West ,1981年冬蔡楓彬印度Trisul , 1982年林芳娟尼泊爾Tent Peak女子隊, 1982吳夏雄印度白針峰, 1983李淳容印度Brigupath 新路線張銘隆登頂等喜馬拉雅6000及7000公尺級登山活動。這段期間以至往後十年,台灣山岳界把目標往上放向8000公尺巨峰, 1993年5月傑出的李淳容女士組織兩岸珠穆朗瑪峰登峰隊,吳錦雄成為第一個台灣人登上世界最高峰 - 聖母峰。
散居各地,漂泊無定所, 並無特定組織型式, 以活動為旨趣凝結,回顧「雪岩俱樂部」60年代末開始萌芽, 到80年代中期, 前後達25年的台灣海外登山的黃金時代, 這些當年的「救難英雄」幾乎無役不參。是年在玉山救難的這些隊員, 不但活躍在喜馬拉雅,也多有北美阿拉斯加及南美安地斯的探險登山活動。
不過, 上天並不獨厚這群仁者,大貓在1982年一次車禍中嚴重腿傷,隔年倆位傑出隊友徐慶榮及黃世傑同時在印度喜瑪拉雅的登峰途中失蹤,至今杳無音訊。
去年到苗栗馬拉邦山弔念徐慶榮, 今年(2005)初大貓自美返國,再度勾起了昔日山中共患難的記憶。
始作俑者之一的我, 心想不能忘懷台灣登山史上這一段… 。
讓榮譽歸於勇者, 讓事蹟永留世人; 山岳無情, 前事已難避免,有期後者知所警備,是筆者所願。
張文溪
2005年6月5日
遇難現場實況—
元月二十九日下午4時 –6時
[第一現場] 「劍溝」底部
「劍溝」底部, 海拔約3600公尺。 「劍溝」為玉山鋸齒岩綾(往東峰方向)的第一道岩溝, 寬度約100-200公尺, 自綾上以50°-30°之坡度垂下約200公尺長, 若從峰頂計算高差400公尺。劍溝底部稍呈緩降坡勢, 匯集兩側雪量, 元月二十九日之積雪約2公尺深。
林從峰頂失足掉落在50°-30°之北壁上, 最後彈跌駐停在「劍溝」底部成Y狀之雪坡上, 王文魁冒險抵現場時發現林已經身亡。 隨王下崖之郭也失足掉落在離喪身林不遠處, 郭多處出血, 無骨折現象, 但頭部重創, 傷口很深, 已昏迷不醒, 有腦震盪, 尚有氣息。 王在雪坡上利用冰斧挖雪洞與郭一起擁抱保暖。身邊無飲水、食糧及禦寒衣物。
[第二現場] 玉山北壁上
玉山頂下約100公尺處, 受困於北壁上的黃森霖, 背負著睡袋與糧食下崖救援的黃身困在冰雪岩複雜地形的北壁上進退不得。留守山頂上之許與唐兩人無力救援。 當時晚上6時。
[第三現場] 玉山頂
許聰文見狀獨自下山求援, 獨留唐淑芬一人在頂峰帳篷內。 約下午六時, 許從風口冒風雪摸黑找到設在「主北鞍部」已進駐第四天的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冬訓前進基地營(ABC)。 該冬訓隊伍為先遣隊長清大體育老師應詩澄領軍, 副隊長謝世枋, 隊員黃福來、王明源、蕭宗熙、洪端祐及冬訓營總策劃張文溪一共七人。
[第一現場] 「劍溝」底部
「劍溝」底部, 海拔約3600公尺。 「劍溝」為玉山鋸齒岩綾(往東峰方向)的第一道岩溝, 寬度約100-200公尺, 自綾上以50°-30°之坡度垂下約200公尺長, 若從峰頂計算高差400公尺。劍溝底部稍呈緩降坡勢, 匯集兩側雪量, 元月二十九日之積雪約2公尺深。
林從峰頂失足掉落在50°-30°之北壁上, 最後彈跌駐停在「劍溝」底部成Y狀之雪坡上, 王文魁冒險抵現場時發現林已經身亡。 隨王下崖之郭也失足掉落在離喪身林不遠處, 郭多處出血, 無骨折現象, 但頭部重創, 傷口很深, 已昏迷不醒, 有腦震盪, 尚有氣息。 王在雪坡上利用冰斧挖雪洞與郭一起擁抱保暖。身邊無飲水、食糧及禦寒衣物。
[第二現場] 玉山北壁上
玉山頂下約100公尺處, 受困於北壁上的黃森霖, 背負著睡袋與糧食下崖救援的黃身困在冰雪岩複雜地形的北壁上進退不得。留守山頂上之許與唐兩人無力救援。 當時晚上6時。
[第三現場] 玉山頂
許聰文見狀獨自下山求援, 獨留唐淑芬一人在頂峰帳篷內。 約下午六時, 許從風口冒風雪摸黑找到設在「主北鞍部」已進駐第四天的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冬訓前進基地營(ABC)。 該冬訓隊伍為先遣隊長清大體育老師應詩澄領軍, 副隊長謝世枋, 隊員黃福來、王明源、蕭宗熙、洪端祐及冬訓營總策劃張文溪一共七人。
應用人身雪橇來送下傷患
訂閱:
意見 (Atom)